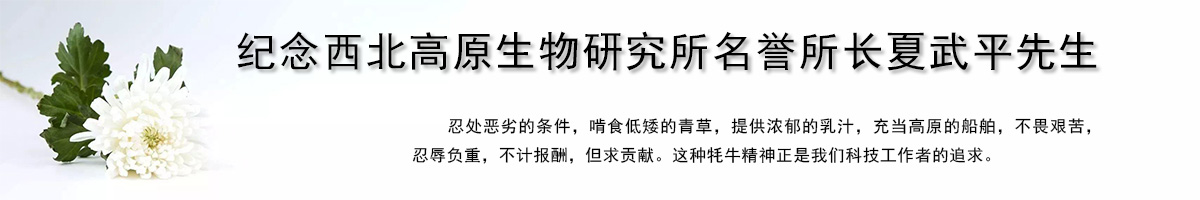常思金露梅
-记夏武平先生
夏武平(1918—2009)河北柏乡人,1945年毕业于私立燕京大学生物系。历任原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室主任。1966年调到青海高原,历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动物生态室主任、所长;1978年起,曾担任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兽类学会理事长,是《兽类学报》、《高寒草句生态系统》、《高原生物学集刊》主编、《生态学报》副主编。他是中国著名的兽类学家和动物生态学家,我国兽类生态学和啮齿动物生态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夏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接受国家任务,开始进行鼠疫防治的研究工作,并从事啮齿动物分布、习性及生活史的调查与研究,成为中国科学院首位涉足动物流行病研究领域的推动者。1952年美军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夏先生参加反细菌战工作,根据他以往的分类成果,鉴定出是美军所投一种小田鼠所携细菌的结果,作为“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报告附件”,成为制裁美军细菌战的有力佐证。从此,夏武平一举成名。他扎根青海高原,冲破阻力,在西高所率先成立生态研究室,并在海北建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开创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先河;在他的组织领导下,以新疆小家鼠大爆发为契机,连续16年对小家鼠进行了观测,使我国的生态学研究水平接近了国际水平。他还通过大量调查研究,首先提出了“凡鼠都有害的观点是错误的” ,“鼠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是十分复杂的”观点,对农林牧和卫生系统等领域的鼠害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他多次撰文提出鼠害治理的生态观,认为鼠害多在生态失衡的情况下产生。他在晚年双目失明的状况下,忍受寂寞和痛苦,继续为中国兽类学的科学发展思考,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生态学事业。
高原牛羊不怕寒,东海水母上山巅。任是大风卷沙暴,犹有鸿雁领头斑。但见青海湖水碧,不知湟鱼生活难。江河源头风光好,瘦马夕阳影如山。
常读夏先生的旧体诗《迎七一》,思绪万千,感慨不已。那是夏武平先生于1980年6月为庆祝党的生日所作。当然,我知道诗中的“水母’’是所指顽强生存在高原的水母雪莲,“头雁”即雁类中的青藏高原特有种斑头雁。夏先生并不是诗人,但他却用诗人的激情,生动形象地概括了青海高原的美丽山水和奇特物种。从中我也品味出一个中国生态学家对高原环境的担忧和企望。写诗的那年,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对高原的未来,却充满了自信。
我投身高原生物事业时才25岁,进所不几天,被分派到“高原鼠兔生物学习性及生态研究”课题组,在隆冬季节,前往海西天峻草原和牧民群众一起,开展药物灭鼠,开始了边学习边操作的新工作。两年后的一天,同事们吵吵着说,所里来了个夏先生,是全国有名的“老鼠头儿”。1962年和中国的“兽头”寿振黄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所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态研究室,他却抛下条件优裕的北京,兴致勃勃地来到青海,参与高原生态科学研究的统领工作。
48岁的夏先生,精力旺盛,穿着朴素,多年都是一套蓝色或灰色的中山服。只是他的眼睛与众不同,修长的眉善良的眼,仅能看得见正前方的一圆圈景物。这一折磨人的顽疾还是受他父亲的遗传因素所致。夏先生的父亲夏纬瑛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植物分类学家,喜诗歌与书法,由于眼疾,早年失明。1966年,他有《视衰》诗一首曰:“曾查秋毫末,迄不减舆薪。明敏少年事,昏瞀老来身。尚能知寒暖,聊以感旧新。东风扑面至,青草自己春。”
夏纬瑛老先生是早期北京农大农业生物系的职员,有幸曾跟随许多中外科学家在华北、西北,寻山问水,实地考察和采集植物标本。从此得到走向学术界之机遇,自学植物分类学,喜爱钻研显微技术。他在发表“黄山松新种”时,曾作过叶面的组织学描述,故有《视衰》诗中“察秋毫”一句。夏老先生50岁后,专门从事植物学史与农学史之研究,他对《本草纲目》的研究成果,致使他名声大噪。
夏武平由于老父亲的严教,年少时在故乡河北柏乡入私塾学古文习算术,然后入中学,住校锻炼自立能力。后来考入了私立北京燕京大学生物系。记得夏先生给我说过,抗战期间,学校南迁,辗转至重庆时,生活维艰,由于他有英语基础,便一面上学,一面给援华美军军官团用英语教授汉语,挣些薪水填补生活,如此,也迫使他提高了英语口语能力。1945年抗战胜利,他也毕业了,回到北平先在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从事腹足类和鱼类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接受国家任务,开始鼠疫防治的研究工作。我国东北,在1910年10月初发生鼠疫,到10月25日,满洲里也首发鼠疫,至11月8日起,鼠疫传至哈尔滨,随之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至日伪时期,东北仍然时有发生。
夏先生深入东北林区,开始从啮齿动物的分布、习性及生活史进行调查研究,成为了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机构首位涉足动物流行病研究领域的推动者。1952年,侵朝美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中科院当即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调查。夏先生前往东北鉴定出一种美军空投的小田鼠,携带鼠疫杆菌,结果公布于“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附件”中,对揭露和声讨美军违反国际法使用细菌战,拿出了有力的科学证据。这一成果的基础,当然是由于夏先生在东北对研究工作的极端负责,他几年来的啮齿类调查作为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之后,夏先生依然在东北大小兴安岭日夜奔跑,进行了小兴安岭红松直播防治鼠害的研究和流行性出血热宿主动物调查,带岭林区鼠类种群数量动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等一系列有关啮齿类动物生态学论文,连续发表在《动物学报》上,这是国内最早开展的动物系统观测工作。由于他对反细菌战的贡献、著名的十篇论文,因此使年轻的科学家,被科学院破格授予研究员资格。同时,被派为访问学者,走访了北非、东欧十国,影响遍及国际生物学界。在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所发生的鼠疫大灾难,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后来,夏先生根据在东北林区22年的观测资料,所提出的数值模型分析,发现棕背鼠平三年出现一次数量高峰的变动规律。这对推动我国鼠类种群生态学的发展起着先导作用。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诗中感慨地说:“常绿松山林中楼,永翠河水潺潺流。二十年资料出规律,鼠害预测居上游。”鼠疫与鼠的关系常常被人们所重视,但鼠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在生物链中的生态关系,所起的重要作用,却被人们所忽略。老鼠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老鼠偷油、盗粮、啃树、噬牧草、传播疾病,老鼠是“四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都是人们厌恶鼠类的理由。可是,夏先生成为“老鼠头”之前,早在1962年,就和寿振黄先生共同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动物生态研究室,主要通过种类和数量较多的鼠类为生态研究的代表种类,发展中国的兽类生态学。他首先提出了组建鼠类生态学研究组的规划,明确以种群动态及其调节研究为核心目标,积极从野外种群观测、实验生态与鼠害防治实践方向寻求相结合的发展空间。内蒙古草原面积辽阔,农业耕区交错其间,黄鼠、旅鼠、达吾尔鼠兔等鼠类种类数量很多,已经形成了对农牧业的危害。1963年,他前往内蒙古农牧区进行调查,萌生在青海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区建立两个长期生态定位站的想法。那时,夏先生有诗《朝沐》记道:“朝沐饧林水,夕宿蒙古包。不怕风霜苦,何畏烈日灼。草原科学建,尖兵意志高。心慕大庆人,为国立功劳。”此诗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艰苦搞生态研究的心境可见一斑。
西高所几年来所进行的生物区系调查和鼠类生物学研究工作的进程,夏先生是了解的,他于1966年主动请求调到青海,率先在生物所成立了生态研究室。那时,我们动物室已经根据当时的生产需要,建立有高原鼠兔组、鼢鼠组、昆虫组,结合防治进行生态研究。有一次他给我们说,我们国家的动物生态研究与美国及先进国家,差距有30年,我们再不搞就难以赶上他们,工业好赶,生物学就难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生态动物研究工作先以种群数量最多,危害牧区生产最为严重的高原鼠兔开始,围绕着鼠兔研究,对高原地区产草量、草原退化、气候变化等等一系列的生态研究项目,开始在青海省海西、海北、黄南等地区定点进行。夏先生亲自带领几个年轻人,通过调查选点,决定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建立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推动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开创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的先河,实现了他的多年愿望。后来在他的组织下,汇编近20年的科研成果,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灭鼠与鼠类生物学研究报告》4集,《高寒草甸生态系统》4集,这几百篇论文,内容包括鸟、兽、虫、鱼和植物及土壤、寄生虫、微生物与气象等,对后来高原生态学研究的发展与世界接轨打下了坚实基础。1984年,夏先生提出在极端环境影响下兽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产生适应性;他提出生态系统中能流物流的作用,天敌或寄生虫与疾病对动物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作用,兽类的化学通讯,以及种群动态、最佳获取量等一系列研究方向,为开创中国特色的以“鼠类种群生态学研究与鼠害治理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0年1月,夏武平请来他的老父亲夏纬瑛先生为生物所讲课。严寒的高原并没有使老先生畏惧,西上青海高原是他多年的夙愿,他初到西宁,便心情激动地留下了诗作《赴西宁》,诗中他欢快地唱道:“昔日频作陕甘游,数经霸桥过渭河。关中四寨连华岳,秦川八百接崆峒。六盘山下白杨树,五道河边红柳丛。于今不复走老路,火车直驰到西宁。”夏老先生双目基本失明,所里派人将瘦弱的老先生背到研究楼会议室。老先生给大家讲了他上世纪初在华北西北考察时的动植物见闻及植物分类,使大家对那时的西北地貌有了一种较为形象的了解和对比。虽然那会儿时局动荡,战烟未消,但落后的西北经济中,大自然的景观仍然保留有一种质朴的尊严。但夏老先生在一次讲述他的成果《<本草纲目>辩证研究》时,已经谈到了盲目开发资源,使得自然生态趋向失衡的担忧。夏老先生声音爽朗,措辞清新,内容简洁,深入浅出,赢得一阵阵热烈掌声。我聆听老先生的讲课,方才晓得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学者,如何将自己的思想阐述得那么生动自然。
他那看不见的瞀眼在说到大西北的地域自然美景时,竟然是炯炯有神,好像在释放光芒。正如他在《西宁杨柳》一诗中所说:“西宁也载杨柳树,春来发叶色青青。莫道高原景光异,世上到处有东风。”他对青海高原的未来充满信心。
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疆地区,发生大面积鼠害、虫害和鸟害,地域辽阔的北疆农牧区,向来是广种薄收,人们对许多鼠类、鸟类和蛇类的生态与防治都不甚了解。经新疆农牧业领导机关的请求,中国科学院派遣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和北京动物研究所联合前往新疆,解决生物灾害问题。西北高原生物所首当其冲担负起灭鼠防鼠的重要任务。我们课题组抽调出朱家贤、朱盛侃、狄淑兰和我四人,春节刚过就赶往乌鲁木齐市,在新疆灭鼠治蝗指挥部领导下,与新疆从事农牧、园林、防疫等部门科技人员,选点到受灾最为严重的昌吉州玛纳斯县,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动物所的朱靖、冯祚建,成都动物所的赵尔宓等科学家在塔城和伊宁地区调查蛇害鸟害。那时,夏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仍然时刻关心着我们的防治工作。
昌吉回族自治州所辖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米泉、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八县,犹如一字儿沿着巍峨的天山,撒开的一串绿色珍珠,物产丰美,是新疆主要的农区。1968年突然爆发的鼠灾,致使大面积农业减产,有的生产队甚至绝收,仅北疆农区损失粮食3亿多斤。我们走访各县,农民见了都说:“几百亩的条田,麦子眼看成熟,穗头沉甸甸的,真让人欢心。我们请上亲戚邻里相约好明天去开镰收割,第二天早晨坐着马车到地里割麦呢,看到的……嗨!条田里齐刷刷的没有了一个穗头.只剩下一片片麦杆子!”渴望丰收的人们在一个个一望无际的条田内,看到的竟然是如此情景,使带着工具兴冲冲而来的主人和亲友们,有的失声痛哭,有的深感恐惧。啊,胡大呀,难道是你让我们辛辛苦苦一年所得的食物或财富,让神鬼给收走吗?为啥在人心混乱的年份,老天又降磨难给百姓?但是,仔细的人到地里看到了黑黑的一层鼠粪,见到了许许多多像自行车胎压过的痕迹,这才明白,夺走我们粮食的神鬼就是老鼠,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
我们一面进行大面积长距离的定点调查,了解到鼠害发生高峰期,小家鼠大量进人室内,啃坏保险柜内的文件,咬伤解放军战士的鼻子,吃净农民挂在梁上篮子里的猪头,面柜、口袋、缸里的存放的粮食,一多半是老鼠粪便;被子衣服鞋袜都被咬成了洞。我们一面撰稿刻印《灭鼠治蝗简报》,向全新疆农牧区州县防治站、区乡政府和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同时,组织群众开办学习班,讲解鼠类生态知识和使用化学毒剂灭鼠的方法,带领群众在农田地头、家院房屋、乡镇粮库以及林带、果园、水库、水渠投放磷化锌毒饵。在牧区由动物所专家进行灭蛇、灭蝗虫、灭乌鸦、灭草原害鼠的工作。进入秋季时,在塔城草原上,群众所挖的灭蛇洞内,一天就能用木棍捣死一二百条“箭杆蛇”,即一种三四十厘米长的蝮蛇。一种白脖乌鸦飞过来,有如一大片黑乌云,顷刻工夫,大片玉米地里便会颗粒无收。
后来,夏先生也来我们在塔西河地区工作点,和我们一起每天都要采集许多老鼠,分类解剖。什么根田鼠、小家鼠、灰仓鼠、黄旅鼠、大沙鼠和柽柳沙鼠等等。我们穿着白大褂,解剖测检,登记体长体重、子宫角、胚胎数、胃存食糜,还有头骨、牙齿、眼眶等等一系列数据,来推算鼠类年龄结构、繁殖次数、种群数量等。食堂做饭的大娘说:“看你们一个个从北京、青海省城来的教授专家,文邹邹的像个医生,可做的事儿是谁也不干的抓老鼠的事情,死老鼠臭烘烘的,唉,这怎么说呢?”“大娘,要没有这些人搞这些臭烘烘的事情,这鼠害、虫害就没有人管,就要祸害咱们农民,老百姓就吃不上香喷喷的饭。”夏先生略带幽默的话语让大娘笑了起来。
那时候,人们都在忙着打派仗,农村也不例外。玛纳斯县塔西河只有一个秘书和会计留守。乡村缺医少药,我会些针灸和一般的中医处方,也教会了几个同事,给上门的农民扎针治疗关节炎、腰肌挫伤、以及月经错期、白带过多等简单的疾病。但由于我们服务态度好,针灸也能治疗成功几种疾病,病人越来越多,每天由夏先生编号30个看病,但人们都要找夏先生看,因为他们认为年纪大的老大夫看病本事最大,还经常带来些花生、南瓜子,让我们做捕捉老鼠的食饵。但夏先生并不精于此道,最后为了不伤害老百姓感情,我和夏先生出去到各县调查,才让这场戏剧慢慢收场。
夏先生爱诗,我俩在吉姆萨尔的玉米地调查鼠类数量时,已近黄昏,看到硕大的落日映照在芦花荡漾的小湖泊,夏先生命我吟诗,我脱口而说:“夕阳无限好,已是近黄昏。”他说:“诗是应了景儿,但由你说出却不好。应该是‘夕阳无限好,明朝更光辉’”。…其实,夏先生明白我的意思,因为我在阿勒泰温都塔拉灭鼠时,长期带群众拌毒饵,致使药物中毒患严重心脏病,有时情绪会突然变得非常低落,他是在鼓励我看到明天的灿烂阳光。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睛又不好,每每过城镇的马路,他却搀着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街道。
在木垒县时,同事们来接我们。我们见驼绒、棉絮、处理的小地毯、苏联基洛夫手表,都争着买,可是夏先生啥也不买。我们返回到米泉县,已经是傍晚,个个饿得不行,等在一家招待所吃完饭结账时,才发现所有的钱都花完了。管账的组长正要拿出工作证和介绍信去谈欠账事,夏先生阻止住了。他笑吟吟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五元钱来,不但交了我们几个人的饭费,还正够住宿的钱。他的这一留有余地的生活经验,教我受用至今。
无独有偶,1977年夏先生曾给西高所常韬老所长赠诗一首:“老来喜群芳,思乡不归乡。夕阳无限好,因有照明光。”
在夏先生主持下,新疆玛纳斯小家鼠生物学研究与预测预报研究项目坚持了16年,后来虽然我所人员撤出。2007年我再次去新疆时,玛纳斯鼠防站科研人员仍然在继续观察、调查,掌握着小家鼠鼠类种群变动的连续数据,这个已有近40年小家鼠种群动态数据的点,是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国际先进行列。
私下,几个科研人员开玩笑说夏先生这个老鼠头“鼠目寸光”。其实,他很有眼光,爱惜人才,待人大度,具有前瞻性。在文化革命末期,冲破阻力,调进学外语的人才和启用受迫害的罗泽甫,给科研人员举办高中低三种学习班,学习英语、日语、德语;争取指标,让年轻的科研人员出国,或访问或深造,扩大眼界,进行对比,尽力把大家在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抢回来。他倡导成立了中国兽类学会,他主持创办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兽类学报》。他尽可能地给大家创造轻松的环境,让大家心情舒畅地静心研究。夏先生颇具大家风范,提携后人,帮助那些爱学习爱钻研的年轻人。请马世骏等专家及外国的生态学家来所讲课,进行学术交流。他把许多出国考察的机会都给了青年学者。他重学历但又不唯学历,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他常给我讲北京动物所有几个技术人员在组织和专家的培养下成为了研究员,他父亲的几个老同事都是由小学初中程度为起点,后来成为植物所、农土所的有名专家。但我虽然悟出先生语中之道,却怪我不成器,依然梦想走文学之路,枉费了夏先生的一片苦心。后来,他目疾严重,居住北京时,常听广播,当听到我的散文、通讯在中央台播出,向家人及西高所前去看望他的人讲:“我没看错,小辛是个优良品种,走到哪儿都会开花结果。”仍然对我进行鼓舞和鞭策。
我常见有人拿着一摞一摞的论文手稿,请夏先生审阅,先生也常交待活儿帮他打印文稿,抄写论文,那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喜爱他写的钢笔字,也爱读他的论文,觉得那是一种享受,能够学到东西。别看他总管全所研究工作,那么忙,他自己几年中主持参加了“钩端螺旋体病的病源及流行病学研究-长江三峡和湖北神农架自然疫源地调查”、《中国动物志》、“朝鲜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研究工作——昆虫和田鼠部分”等项目,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长爪沙鼠综合防治及应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一、三集分别获得青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那几年先生真是忙啊,他有诗《不得闲》曰:“一从踏上三江源,历经风雨十二年。自怜眼瞎多病躯,犹是攻关不得闲。”正是他的真实写照。
在科学领域,夏先生是有魄力有胆识的人。当人们曾经把“四害”中的麻雀千呼万唤地解救出来以后,全国著名的老鼠头儿、一生致力于防治鼠害的人,怎么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竟然提出老鼠是灭不完的,不是所有的鼠类都会造成灾害。想想,中国十二生肖中鼠为大,那是有道理的。你看,小小老鼠,高山雪地有它的踪迹,南北极冻原有它的身影,荒漠戈壁有它的洞穴,江河湖海有它在活动,甚至连海洋巨霸鲸鱼皮肤上也有老鼠寄生。夏先生多次撰文阐述有关鼠害治理的生态观,他认为“鼠害的发生多数是在自然环境中由于生态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产生的,并随生态系统的演化而变化,鼠害治理应该遵循生态学原理进行,方能根治鼠类的危害。”我看青海草原的鼠害和新疆北疆农区小家鼠大发生就是例证;同时,他大胆提出了“凡鼠都有害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鼠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或功能是十分复杂”的观点,在生物链中鼠类起着其他动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试想,如果我们没有小白鼠作为实验动物,人类所需要的任何新药品就无法产生。夏先生的这一观点,其实对我们在农业、林业、牧业和卫生等领域如何治理鼠害具有指导意义。正如《易经》所贯穿的“一切要顺其自然”的道法。
夏先生从不会在人前做秀,更不善于在会上讲类似政治号召性的话语。可是他以自己在青海高原的切身体会,激励我们“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如画如诗的语言,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青海高原每个科技人员的精神品格。夏先生有诗赞曰:
牦牛笨拙不怕难,生态建站岂等闲。青藏高原缺氧初,西北大地丰产田。十年辛苦初创业,万里草甸何高寒?为学常思金露梅,顶风冒雪遍山峦。(撰稿人:辛光武)